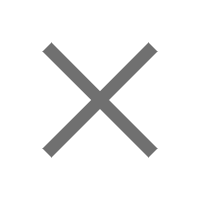“今人不見古時月,今月曾經照古人”,作為(wei) 地球唯一的天然衛星,月球已與(yu) 地球陰晴圓缺相伴了數十億(yi) 年的時光。然而由於(yu) 公轉與(yu) 自轉周期相等,無論月相如何變化,月球始終隻以同一麵朝向地球。受月背通信阻隔等問題的限製,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的月球探測活動,一直局限在對月球正麵的著陸探測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,“到月球背麵去”被視作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務”。

圖為(wei) 嫦娥四號參研參試人員群體(ti) 代表劉適、葉培建、孫澤洲(從(cong) 左至右)
2019年1月3日10時26分,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著陸月球背麵東(dong) 經177.6度、南緯45.5度附近的預選著陸區,並通過“鵲橋”中繼星傳(chuan) 回了世界第一張近距離拍攝的月背影像圖。創造性地實現了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著陸、首次月背與(yu) 地球的中繼通信,開啟了人類月球探測新篇章。
從(cong) “嫦娥一號”到“嫦娥四號”,從(cong) 懵懂起步到引領世界,中國探月工程才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。一大批老專(zhuan) 家和年輕的科研人員,在普通的崗位上恪盡職守、默默奉獻,實現著中國探月工程總目標的乘勝前進。
2019年6月,《榜樣4》節目錄製期間,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培建、嫦娥四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和探測器測控數傳(chuan) 分係統主任設計師劉適作為(wei) 嫦娥四號參研參試人員群體(ti) 代表來到現場。
匆匆的身影,也讓我們(men) 了解到這個(ge) 探月“夢之隊”的輝煌與(yu) 艱辛、夢想與(yu) 執著。

葉培建
現年74歲的葉培建院士生於(yu) 在江蘇泰興(xing) 胡莊鎮海潮,父親(qin) 母親(qin) 都是新四軍(jun) 老戰士。他從(cong) 小隨抗美援朝歸來的父親(qin) 四處輾轉,“部隊到哪兒(er) 就到哪兒(er) ”。從(cong) 青年時期填報大學誌願時,聽從(cong) 父親(qin) 的教誨:“國家正處於(yu) 建設時期,很需要工科人才”,選報了南航、北航等學校,到1985年獲得瑞士納沙太爾大學科學博士後,懷著“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祖國麵貌”的迫切願望回到祖國;從(cong) 在艱苦條件下,為(wei) 開發“紅外熱軸探測係統”背著儀(yi) 器乘火車一站一站采集數據,到用衛星做股票,在衛星應用領域第一個(ge) “吃螃蟹”;從(cong) 擔綱中國“資源二號”衛星總設計師兼總指揮,到勇挑“嫦娥”係列研發重擔。在他身上,充溢著老一輩科學家濃濃的家國情懷和艱苦奮鬥、勇攀高峰的科學精神。
軍(jun) 人家庭的熏陶,長期的科研經曆,也使他養(yang) 成了嚴(yan) 謹的治學態度和高尚的敬業(ye) 精神。對衛星研製技術工作要求精益求精,周而複始求證,“做事沒有‘差不多’”,隻有‘行’和‘不行’。日常時間,他總會(hui) 提前半小時到辦公室,把一天的工作按順序列出。每逢節假日,他總要到試驗現場轉一轉。麵對“禮拜六加班是肯定的,禮拜天加不加班不一定”的工作狀態,他說,“一個(ge) 國家總需要一部分人做出更多的事情”。他大膽啟用年輕科研人才,嚴(yan) 格要求又溫暖關(guan) 懷,他視責任重於(yu) 泰山,將自己發射的衛星看的比生命還重要。他說,人類文明要向前發展,總要有人看得更遠一點。
從(cong) 2001年肩負著“資源二號”的重任與(yu) 中國探月工程結緣;到2004年“嫦娥一號”探月衛星正式立項,帶領著一支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研製隊伍,用短短3年時間完成了“嫦娥一號”衛星的研製;再到如今“嫦娥四號”取得的成績,“飛向火星”的星際夢想,他以隻爭(zheng) 朝夕、時不我待的精神,為(wei) 中國奔向月球以及到更遙遠地方進行深空探測殫精竭慮,“宇宙就是個(ge) 海洋,如果我們(men) 不去,別人去了,別人占下來了,我們(men) 再想去就去不了。”
18年來,這位“人民科學家”見證了“嫦娥”每一個(ge) 振奮人心的瞬間,也深知這些瞬間背後所凝聚的艱辛。他說,“作為(wei) 一名航天人,能夠親(qin) 身參與(yu) 並見證我國航天事業(ye) 的發展,是一種幸福”。
葉培建院士在《榜樣4》節目錄製現場也受到眾(zhong) 星捧月般的簇擁,要求合影的“粉絲(si) ”絡繹不絕。大家笑著說,“我們(men) 都在追星”,葉培建也笑著說,這是有依據的,國際編號為(wei) 456677小行星就叫“葉培建星”。2017年1月12日,為(wei) 了表彰葉培建院士為(wei) 推動我國衛星遙感、月球與(yu) 深空探測及空間科學快速發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,經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推薦、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(hui) 批準,這顆在火星和木星軌道之間繞太陽運行的小行星,被命名“葉培建星”,象征著把像葉培建院士一樣的中國人的探索精神“高懸廣袤星空”。

孫澤洲
嫦娥四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是位“70後”,1992年從(cong)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工程專(zhuan) 業(ye) 畢業(ye) ,來到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。2001年開始與(yu) “嫦娥”結緣,參與(yu) “嫦娥”為(wei) 期三年的前期論證;2004年被任命為(wei) 嫦娥一號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;2008年嫦娥三號探測器係統研發時,年僅(jin) 38歲的他接過“中國探月”的接力棒,成為(wei) 當時航天係統最年輕的總設計師。之後,嫦娥四號探測器任務和中國火星探測任務分別正式立項,孫澤洲被任命為(wei) 兩(liang) 大探測器的總設計師,擔起了一麵飛“月球”一麵奔“火星”的“超常”職業(ye) 使命。
想到充滿挑戰的研發任務,我們(men) 本以為(wei) 在節目錄製期間見到的,會(hui) 是一位麵色嚴(yan) 峻、不苟言笑的“霸道總裁”。意外的是,來到現場的他,身上看不到一絲(si) 沉重和疲憊的氣息。他們(men) 確實很忙,每次都是匆匆而來,匆匆而去,經常排練完還要趕回去加班,但都像葉培建院士一樣,隻要有空餘(yu) 時間,就會(hui) 和大家談笑風生,講探月的故事,講火星的知識,娓娓道來,有問必答,一長串航天數據和專(zhuan) 業(ye) 術語信手拈來。在孫澤洲心裏,“嫦娥”係列的研發並不枯燥。“航天器研製是一份充滿想象力的工作,嫦娥三號要完成什麽(me) 任務,嫦娥四號要增加什麽(me) 樣的功能,未來我們(men) 還可以在哪些方麵進行突破,都充滿想象的空間”,言語中帶著對工作永不止歇的熱愛。
作為(wei) 嫦娥三號、嫦娥四號的總設計師,要對黨(dang) 和人民負責,要麵對全世界的關(guan) 注,孫澤洲說壓力確實很大,但更重要的是事先周而複始進行嚴(yan) 密的論證、細致地測試,“要成為(wei) 一棵‘大樹’,遇到困難的時候,首先把責任擔起來”。他很了解團隊成員,誰來自哪個(ge) 學校如數家珍,問他如何和團隊相處時,他笑著說葉院士做得更好,葉院士連誰家孩子什麽(me) 時候高考都記得清清楚楚。
孫澤洲提到嫦娥每次發射前,團隊都要到西昌封閉90多天,這時臨(lin) 時黨(dang) 支部就會(hui) 發揮作用,一方麵會(hui) 對隊員家裏情況進行事先摸底,了解有無困難需要單位幫忙,以解決(jue) 隊員的後顧之憂;另一方麵會(hui) 進行隊伍建設,如舉(ju) 行塔架下的升旗儀(yi) 式,組織支部結對共建,通過黨(dang) 課學習(xi) ,做好思想工作,保證發射任務的圓滿完成。

劉適
34歲的嫦娥四號探測器測控數傳(chuan) 分係統主任設計師劉適,有著工科男特有的內(nei) 秀和“呆萌”,專(zhuan) 注的神情中,帶著對自己所從(cong) 事工作的濃濃情結。他本科就讀於(yu) 哈爾濱工業(ye) 大學航天學院,懷著對航天工作的興(xing) 趣和熱愛進入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究生院飛行器設計專(zhuan) 業(ye) 學習(xi) ,並在2010年畢業(ye) 後進入航天部門工作。
劉適說之所以選擇航天五院,不僅(jin) 是因為(wei) 專(zhuan) 業(ye) 和興(xing) 趣,更是因為(wei) 這裏良好、單純的工作氛圍,這個(ge) 集體(ti) 中的人對工作的傾(qing) 情投入和不計回報深深感染了他,“有一次,我的導師為(wei) 我指導研究生開題報告,邊改報告邊教我應該怎麽(me) 寫(xie) ,需要注意什麽(me) 東(dong) 西,非常耐心,一直到大約夜裏十二點,我都有點兒(er) 挺不住了。好不容易他改完了報告,跟我說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但他還得留下來,因為(wei) 他自己的工作還沒有完成。”
他說,航天團隊特別有奉獻精神,他們(men) 班組中有兩(liang) 位老大姐,快退休了,曾取得過很多成績,但現在依然在第一線,幹著和年輕人一樣高強度的工作,跟年輕人一起加班。還有一位老大哥,哪裏苦哪裏難,他就出現在哪裏,45歲才有了第一個(ge) 孩子。“這樣的人和事在周圍有很多,很正麵,非常鼓舞人,是我們(men) 年輕人學習(xi) 的榜樣。”
劉適所在的團隊中每年加班時間累計1000小時以上的人不在少數。航天行業(ye) 有句話叫“後牆不倒”,就是說從(cong) 發射那一天倒排工作計劃,每一個(ge) 環節都要保證按時保質完成,特別是關(guan) 鍵節點出現延誤和返工都是不能接受的。比如火星探測任務每26個(ge) 月才有幾個(ge) 合適的時間段可以發射,一旦錯過,就要再等26個(ge) 月。整個(ge) 團隊都處於(yu) 一種緊張的環境中,有時過年都要加班,大家工作起來都很謹慎。
“行業(ye) 外的合作單位在初次接觸我們(men) 的時候,經常會(hui) 非常不適應我們(men) 的工作作風,會(hui) 覺得不近人情。但是正是這種工作作風,保證了我國航天事業(ye) 的高成功率,我國深空探測任務至今為(wei) 止成功率是百分之百,國際領先,也贏得了國際同行的尊重。特別是嫦娥四號實現了國際首次月球背麵軟著陸探測,NASA的局長第一時間發文祝賀”,他驕傲地說到。
《榜樣4》節目錄製時,嫦娥四號探測器任務團隊負責聯絡的龐老師也來到現場。聽著三位代表講述團隊的事情,龐老師笑著說,也許是傾(qing) 注了太多心血,很多探月人都對“嫦娥”係列有著特殊的感情,會(hui) 把它們(men) 比作自己的孩子,親(qin) 切地稱呼嫦娥一號到嫦娥四號為(wei) “大姐”“二姐”“三姐”“四姐”。對探月人來說,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,從(cong) 探測器研發一開始就會(hui) 不離不棄守護始終。也正是對這份對工作的熱愛和深情,對使命的責任和擔當,推動著我們(men) 國家航天事業(ye) 的不斷發展。
(《同學》工作室)

關(guan) 於(yu) 我們(men) 聯係我們(men) 網站地圖 用戶調查
ky体育中心 版權所有